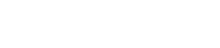.jpg)
【作者簡介】阿音娜(孟秋麗),,歷史學(xué)博士,,中國藏學(xué)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,從事蒙藏關(guān)系史、清代西藏歷史地理研究,。
【文章來源】《中國西藏》2023年第1期,。
在首都北京的幾個(gè)文化機(jī)構(gòu)和高校圖書館,,珍藏著幾幅類似的西藏輿圖,,再現(xiàn)了一百多年前西藏地方與祖國內(nèi)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古道盛景,堪稱清代“漢藏金橋”,。
這幾幅圖分別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,、民族文化宮及北京大學(xué)古籍館,幾幅圖之間存在底圖,、摹本的關(guān)系,。其中國家圖書館藏圖《自打箭爐至前后藏途程圖》標(biāo)有題記,顯示了作者,、繪制背景,,被認(rèn)為可能是底圖存在。日本學(xué)者認(rèn)為可能另有底本,。
該輿圖題名《自打箭爐至前后藏途程圖》,,為絹本彩繪,漢文,,縱41.4厘米,,橫316.3厘米,未注比例,。圖中繪有由打箭爐(今四川甘孜州康定市)出發(fā)入藏的北,、中、南三條路線,。這三條入藏路線都是起至四川打箭爐,,其中北路出北門,由草地直達(dá),,最為捷徑,;中路出南門偏北,,赴察木多(今西藏昌都市),是商人進(jìn)藏常走之路,;南路由理塘(今四川甘孜州理塘縣)——巴塘(今四川甘孜州巴塘縣)——察木多行走,,是駐藏大臣暨各官兵馳驛之所,,即所謂“官道”,,與今日川藏公路及在建鐵路大體相當(dāng)。因南路天氣較暖,,居民稠密,,易于催辦夫馬,但道路較為曲折,。三條路線匯于察木多后,,又分為兩條路線,北路過藏北三十九族轄地后從拉薩北部札什營進(jìn)入拉薩,,南路過墨竹工卡,、德慶等地,從拉薩南門入城,,是為傳統(tǒng)“官道”,。除了用黑色虛線描繪的交通路線外,圖中還用不同顏色及符號畫出了關(guān)隘,、山脈,、河流(雅魯藏布江、怒江,、瀾滄江,、雅礱江、金沙江等)以及行政區(qū)劃,、國界等,。除了交通路線,輿圖還描繪了拉薩,、日喀則,、江孜等地的風(fēng)貌,拉薩三大寺,、布達(dá)拉宮,、駐藏大臣衙門、藥王山,、扎什倫布寺,、江孜等地名和建筑名,顯示了當(dāng)時(shí)對西藏有關(guān)知識的傳播和認(rèn)知,。
.jpg)
國家圖書館藏《自打箭爐至前后藏途程圖》,,圖片來源于《中華輿圖志》
駐藏大臣安成及進(jìn)藏圖
據(jù)題記,,此傳世輿圖作者為駐藏幫辦大臣安成。圖中有一段詳細(xì)的文字題記作為跋語附于圖末尾,,記述繪成此圖的背景及作者簡單經(jīng)歷,。可知,,圖作于辛丑制于1901年(辛丑年),。跋語作者署名為奉命駐藏之仁山,而這一時(shí)期的駐藏大臣字仁山者,,正是安成(1833年一,?)。安成,,字仁山,,滿洲正藍(lán)旗人,1900年時(shí)任四川候補(bǔ)道,、副都統(tǒng)銜的安成被任命為駐藏幫辦大臣補(bǔ)裕鋼(編者注:裕鋼升任駐藏大臣)之缺,,1901年7月到藏,1902年底因病卸任去差,,實(shí)際在藏一年多,。安成赴藏之時(shí),內(nèi)地正值庚子之亂爆發(fā),,西藏也面臨英國第二次武裝侵略之危,,他在這幅地圖題記中說,臨危受命駐藏,,對西藏等地“山川形勢,,疆界毗連,風(fēng)土人情”均不熟悉,,“恐一旦有事,,貽誤地方,關(guān)系非淺,,五內(nèi)焦急,,日夜不遑”,于是“到處咨訪,,考核方輿,,勉繪一圖”,即此清朝官員進(jìn)藏路線圖,。安成在此圖中說,,任職西藏時(shí)已經(jīng)68歲。他離藏后還曾任新疆伊犁副都統(tǒng)兼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,。
地圖上的“漢藏金橋”
該圖右下方題記云:“由爐出口赴藏,,有北,、中、南三路,。”可分為三個(gè)區(qū)段:一是四川段:打箭爐到察木多,。二是西藏段:察木多到拉薩。三是西藏段:拉薩至西藏周邊,。
四川段:
南路:1717年,,準(zhǔn)噶爾軍隊(duì)攻陷拉薩,清朝中央政府收到拉藏汗的告急文書后派多路軍隊(duì)入藏,,其中1719年派定西將軍噶爾弼自成都經(jīng)打箭爐入藏平叛,,開辟了自打箭爐經(jīng)理塘、巴塘,、芒康至察木多的川藏南路大道。戰(zhàn)事結(jié)束后,,1721年,,皇十四子、撫遠(yuǎn)大將軍允禵奏請撤驛改設(shè),,撤自青海入藏之驛站而改設(shè)噶爾弼自打箭爐至藏之驛,,原因是自西寧順?biāo)髁_木路至藏駐驛,冬天寒冷多雪,,驛馬難以生存,,人馬皆有損傷,難以駐驛,。因此川藏線南路日后成為清朝官員常走的入藏路線,,也被稱為“官道”,沿途設(shè)立糧臺,、塘鋪,。我們在地圖中也能看到這條驛路,要經(jīng)過許多山路,,河流,,據(jù)言,有72座山要翻越,。途中還有自北向南流的多條河流阻隔,,因此在中渡等地還有皮船以備行旅,有一定的危險(xiǎn)性,。清末張其勤走到丹達(dá)大山時(shí),,看到山根有丹達(dá)神廟,有馬鞍一具,,靴一雙,,并就此神廟來源寫到:“相傳乾隆年間云南參軍彭某解餉過此,,餉馱誤陷雪窟中,參軍從而殉焉,,土人為塑像祀之”,,張其勤看到的馬鞍、靴都是彭參軍留下的遺物,。據(jù)進(jìn)藏將領(lǐng)言,,從打箭爐入藏到拉薩5300余里(編者注:此處的“里”應(yīng)為華里),軍站一百三十余站,,當(dāng)時(shí)要兩個(gè)月左右的時(shí)間,,如遇意外情況,也有三個(gè)月到藏的,。
北路:可稱草原之路,,從打箭爐北門出關(guān),經(jīng)德格草地,、類烏齊至前藏,。這條路從地圖上看,由于北部都是開闊的草原地帶,,沒有高山,、河流之阻,最為快捷,。但所經(jīng)沒有打尖,、驛站的設(shè)置,供給不便,。
中路:也稱商貿(mào)之路,,出南關(guān)偏北路之南平行過霍爾五家土司:章古土司、白利土司,、麻孜土司,、孔薩土司、朱窩土司之地,,疊蓋土司界,、納多土司界,經(jīng)草地至察木多進(jìn)藏,。此路所經(jīng)土司之地甚多,,圖中詳細(xì)標(biāo)出各土司之名稱及轄域,為研究四川土司不可或缺的資料,。
西藏段:
北,、中、南路匯于察木多,,后又分為南北兩路,,直至拉薩,。其中南路為官道,北路要經(jīng)過藏北草原三十九族地域至拉薩,。
入藏后,,該圖又繪出藏內(nèi)三條交通路線:一條由拉薩經(jīng)曲水分路,北路捷徑沿山腳直達(dá)后藏,,但沒有標(biāo)出地名,。南路經(jīng)白地直達(dá)后藏。到后藏又分出兩路:北路拉薩——日喀則——阿里一線,,與絲綢之路平行,,可謂詳實(shí)稀缺之圖。南路經(jīng)乃黨,、彭措嶺,、協(xié)噶爾(今西藏定日縣協(xié)格爾鎮(zhèn)),定日到聶拉木,,近廓爾喀界,。從定日分出一路,向北經(jīng)宗喀到濟(jì)嚨,。另外由前藏到哲孟雄(即錫金)、布魯克巴(即不丹)界也有兩條路:一條直奔南路,,經(jīng)干壩到大吉嶺附近,,近哲孟雄界。一條由白地直達(dá)布魯克巴界,。這幅圖畫出的幾條交通線,,除了官道和常用之路外,一些交通線并沒有在文獻(xiàn)中記載,,大概如前所述,,是作者通過“到處咨訪,考核方輿”得來的,,可能是民間或貿(mào)易小道,。但無一例外,繪制出直通西藏邊界的各個(gè)要路,,顯示出繪制者所生活時(shí)局下的“邊境情懷”,。
“漢藏金橋”的歷史作用
官員之路: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溝通的金橋。駐藏大臣是代表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管理權(quán)力的官員,。據(jù)史料記載,,清朝時(shí),清朝中央政府派駐大臣到任100多人,,與達(dá)賴?yán)?、班禪額爾德尼地位平等,,共議藏事。這一百多人穿梭往來于官道上,,譜寫著西藏與內(nèi)地溝通的歷史,。從進(jìn)藏官員留下來的記錄來看,駐藏大臣進(jìn)藏履職及卸任回京走的都是川藏官道,,即圖中南路一線,。道光年間駐藏大臣鐘方有《駐藏須知》一書流傳,詳細(xì)記載了清朝官員入藏沿途有18站更換夫馬處,,分別是:中渡,、理塘、巴塘,、南墩,、阿足、乍丫,、昂地,、王卡、包墩,、察木多,、恩達(dá)寨、洛隆宗,、碩板多,、邊壩、拉里,、江達(dá),、墨竹宮、德慶,,輿圖中也標(biāo)出了這18處,,同時(shí)通過輿圖也看到,及至清末,,隨著政局的不斷變化,,川藏驛路又增加了不少站點(diǎn),加快了信息流動和情報(bào)傳遞的速度,,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(guān)系更加緊密,。
商貿(mào)之路: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金橋。驛站交通的鋪設(shè)和發(fā)展客觀上還帶動了驛站沿邊地區(qū)的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,,一些自然形成的商貿(mào)之路也同樣作為一種交流通道延續(xù)百年,。由打箭爐經(jīng)道孚、甘孜、德格,、江達(dá)至昌都的茶馬古道,,習(xí)慣上被稱為“川藏商道”,即本圖中的北路路線,。該路與中路是一條平行的道路,,只不過中路要經(jīng)過土司之地,有一定阻隔,。因此北路,、中路都可稱為商貿(mào)之路。與官道由昌都合,,又分為兩路,。一路由昌都經(jīng)洛隆宗、邊壩,、工布江達(dá),、墨竹工卡至拉薩;一路由昌都經(jīng)三十九族至拉薩的古代茶道,。“道路相望,,歡好不絕”,這條茶馬古道上除了茶葉,、馬匹等物的交流,,也有西藏與內(nèi)地各民族的“金玉綺繡,問遣往來”,,并形成了沿線諸多的貿(mào)易重鎮(zhèn),。比如本條驛路的起點(diǎn)打箭爐,位于大渡河支流雅拉溝與折多河會流處,,西循折多河通理塘、巴塘,、察雅,、昌都與西藏各部,是清代川茶輸藏的集散地和茶馬古道的交通樞紐,??滴跛氖荒辏?702年),清政府在打箭爐設(shè)立茶關(guān),。“其地本非市場,,自宋元以來,隨茶馬貿(mào)易,,日趨繁盛”,。清康雍時(shí)期通過在此設(shè)驛站、糧臺、置廳,,“漢人來此經(jīng)商領(lǐng)墾者漸眾,,市場勃興”。“四方商賈輻輳,。為川茶夷貨交易之所”,,察木多是交通要沖,是多條進(jìn)藏路線的匯合點(diǎn),,為進(jìn)藏門戶,。駐藏大臣聯(lián)豫、張其勤途徑此處時(shí)均認(rèn)為“他日鐵路既通,,必當(dāng)成一巨鎮(zhèn)”,。
軍事之路:維護(hù)邊疆安全、促進(jìn)民族融合的金橋,。清前期為了維護(hù)西藏安全,,曾多次用兵西藏??滴跷迨吣辏?718年),,為了平定準(zhǔn)噶爾之亂,清軍分多路向西藏進(jìn)軍,。其中定西將軍噶爾弼出四川,,走的是理塘、巴塘,、察木多一線,,即圖中南線官道。雍正元年(1723年)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,、雍正五年(1727年)平定阿爾布巴叛亂,、乾隆十四年(1749年)平定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亂等進(jìn)藏軍事行動,也都有軍隊(duì)利用了這條官路,,在清軍平定西藏的過程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,。同時(shí)該條進(jìn)藏路線進(jìn)入西藏后又南延幾條路線至周邊邊境地區(qū),對鞏固國防,、維護(hù)邊疆地區(qū)的安全,,作用重大。乾隆年間廓爾喀兩次入侵后藏,,清軍利用進(jìn)藏路線的南延段,,從該路進(jìn)軍西藏邊境,并在打箭爐,、理塘,、巴塘,、察木多、拉里,、拉薩等六處安設(shè)了糧臺接濟(jì)軍需,,在這條海拔最高、路線最長的道路上上演了驅(qū)逐侵略者,、安輯邊境,、維護(hù)主權(quán)的歷史佳話。軍事之路也促進(jìn)了民族融合,。清代入藏官員記載到:“是以駐藏兵丁例得期滿換班,,亦有屆期不愿更換、甘心老死口外者,,至五六十歲以外,,其飲食起居、語言,、狀貌予番人無異,。或遇內(nèi)地人告以室家子女尚存無恙,,其意似茫然不甚省憶,。”駐守兵丁的一部分已經(jīng)與藏地女子通婚,融入到當(dāng)?shù)氐纳钪辛恕?/p>
.jpg)
國家圖書館藏圖局部“前藏段”,。圖片來源于《中國古代地圖文化史》,,中國地圖出版社2013年出版
融合之路:青藏高原文明融入中華文明的金橋。西藏相對閉合型的自然地理環(huán)境,,西北高,、東南低并自西向東逐漸傾斜的地勢特點(diǎn),決定了西藏西部地形環(huán)境的相對封閉和其東部地形環(huán)境的相對開放,。西藏東部方向的地形及交通條件是其與祖國內(nèi)地東向聯(lián)系的天然基礎(chǔ),。無論是早期文明時(shí)期還是進(jìn)入文字記載時(shí)期以來,西藏與祖國內(nèi)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續(xù)不斷,。尤其到了清代,,這種融合通過一條條進(jìn)藏通道而變得愈發(fā)深入。政治層面,,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,任命駐藏大臣,、駐扎軍隊(duì),,冊封達(dá)賴?yán)铩喽U額爾德尼等大活佛等,,宣告了主權(quán),。民間層面,則有茶馬古道等民間通道進(jìn)一步促進(jìn)了西藏與內(nèi)地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,青藏高原文明最終融合到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圈中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