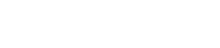[編者按]我館的“豐功偉業(yè)——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”特展開展至今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參觀熱潮,。此次展覽所設立的“藏醫(yī)藥的傳承與發(fā)展”板塊引起了觀眾的極大熱情。在許多人看來,,藏醫(yī)與藏藥充滿了神秘色彩與巨大的吸引力,。為滿足大家對藏醫(yī)藥知識的渴求,接下來的幾期,,就讓我們揭開藏醫(yī)藥的神秘面紗,。
藏醫(yī)藥學的發(fā)展歷史
藏醫(yī)藥學發(fā)源于青藏高原,具有3000多年的發(fā)展歷史,。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,,藏族人民為了防病治病過程就地取材,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具有完整理論體系和豐富臨床經驗的藏醫(yī)藥學體系,。它凝聚了藏民族長期同疾病作斗爭的寶貴經驗,,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,是藏民族文化與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不斷相互適應的產物,,是中華醫(yī)學寶庫中的一顆燦爛奪目的瑰寶,,內容豐富,歷史悠久,。
藏醫(yī)藥學的發(fā)展主要經歷了五個階段:
一,、萌芽時期(遠古~公元6世紀)
約在3000年前,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上業(yè)已開始了原始醫(yī)藥保健知識的積累,,形成了藏醫(yī)藥學的萌芽階段,。他們已經有用火、石針,、原始住房等保健知識,,也就是原始的醫(yī)療保健。
同時,,簡易的涂抹,、酥油止血、青稞糟消毒等實踐技術也為現有的放血,、火疚等獨特治療技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,。

(卡若遺址出土的骨錐、骨針,、骨網墜,。在卡若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磨制得非常漂亮的骨針,說明當時的人已經有縫紉技術,。圖片來源:國家博物館網站)

(雙體陶罐,,出土于昌都卡若遺址,制作工藝純熟,代表了卡若文化的制陶水平和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,,是新石器時代西藏陶器的代表和點睛之作,。圖片來源:西藏博物館網站)
二,、奠基時期(6~9世紀)
公元7世紀,,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,建立強大的吐蕃王朝,,并邀請周邊其他民族的醫(yī)學家和譯師,,配合西藏醫(yī)藥學家,吸收印度醫(yī)學和漢族中醫(yī)藥精華,,整理編著了大量醫(yī)學經典著作,,建立了完善的藏醫(yī)藥理論體系。特別是公元7世紀初,,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一大批漢族中醫(yī)藥書,,對藏醫(yī)藥學的形成和發(fā)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公元8世紀藏醫(yī)藥學歷史名著《四部醫(yī)典》的出現,,標志著藏醫(yī)藥學作為獨立的醫(yī)學理論體系最終形成,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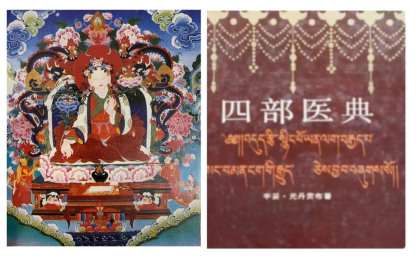
(宇妥·云丹貢布(708~833)是吐蕃王朝時期最杰出的醫(yī)學家,曾擔任贊普的御醫(yī),,是當時藏醫(yī)發(fā)展的最主要代表者,。他根據藏民族自身醫(yī)學體系,借鑒印度等其他醫(yī)藥學精華,,編著了以《四部醫(yī)典》為主的藏醫(yī)藥學典籍30余部,。圖片來源:蔡景峰《藏醫(yī)學通史》,青海人民出版社,,2002年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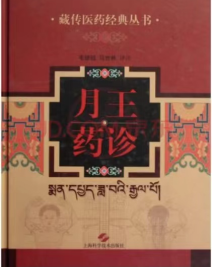
《月王藥診》成書于公元8世紀中期,,是現存最古老的一部理論、實踐和藏藥齊備的藏醫(yī)藥經典著作,。其內容借鑒和吸收了中醫(yī)藥及古印度,、阿拉伯醫(yī)學的精華,也是一部醫(yī)學百科性質的古代醫(yī)學著作,。
三,、爭鳴和發(fā)展時期(9~17世紀)
15世紀,隨著醫(yī)療實踐的發(fā)展,,藏醫(yī)藥學逐漸形成了北方和南方兩大派,。北方派稍早于南方派,以強巴·朗杰扎桑為代表,,南方派則以舒卡·年姆尼多吉為代表,,他們分別總結了北部高寒地區(qū)和南部河谷地帶多發(fā)疾病及其治療經驗,并各有效驗。學術爭鳴的出現標志著藏醫(yī)藥學思想發(fā)展到一個新的階段,。

(圖從左到右分別為:藏醫(yī)北方學派創(chuàng)始人強巴·朗杰扎桑,、南方派創(chuàng)始人舒卡·年姆尼多吉,圖片來源:蔡景峰《藏醫(yī)學通史》,,青海人民出版社,,2002年)
四、繁榮時期(17~20世紀中葉)
五世達賴建立甘丹頗章政權,, 在大力弘揚佛法的同時重視發(fā)展藏醫(yī)藥學,,采取了許多重大措施使藏醫(yī)藥學發(fā)展進入鼎盛時期。這一時期,,藏醫(yī)在醫(yī)療,、教學及對《四部醫(yī)典》的研究發(fā)掘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績。同時,,藏醫(yī)學不但在西藏地區(qū)得到發(fā)展,,而且在西康、 安多,、內蒙古等地也有較大發(fā)展,。
.png)
(第司·桑吉嘉措,圖片來源:蔡景峰《藏醫(yī)學通史》,,青海人民出版社,,2002年)
出生于十七世紀中葉的第司·桑吉嘉措,是藏學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學家,、醫(yī)學家,。他整理了《四部醫(yī)典》,編撰《四部醫(yī)典藍琉璃》,;創(chuàng)辦藥王山醫(yī)校,,發(fā)展藏醫(yī)教育;總結藏醫(yī)歷史,,撰寫《藏醫(yī)史》,;主持繪制唐曼(醫(yī)學掛圖)。第司·桑吉嘉措的醫(yī)學著作和創(chuàng)造發(fā)明,,都是藏醫(yī)發(fā)展史上的里程碑,,影響深遠。
.png)
18世紀,,著名醫(yī)學家帝瑪爾·旦增彭措廣泛收集藥物標本,,編著了《晶珠本草》,成為舉世公認的藏藥本草學巨著,。該書收錄了2294種藥物,,并對藥物的性味、功效以及異名等作了詳細闡述,同時糾正了一些本草學家的錯誤,,為藏醫(yī)用藥,、鑒別以及研究藏醫(yī)藥學做出了突出貢獻。
.png)
(圖為西藏自治區(qū)藏醫(yī)院,。這所醫(yī)院的前身是拉薩市藏醫(yī)院,,市藏醫(yī)院的前身是舊西藏的"門孜康",圖片來源于網絡)
公元1916年,,十三世達賴喇嘛創(chuàng)辦“門孜康”(醫(yī)算局),,廣招門徒,,教授醫(yī)藥理論,,對藏醫(yī)藏藥發(fā)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。從此,,藏醫(yī)藥進入了一個新的發(fā)展階段,。
五、新生和振興時期(1951年以后)
隨著西藏的和平解放及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,,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藏醫(yī)藥的搶救,、繼承和發(fā)展。根植于雪域高原的藏醫(yī)藏藥因此步入大發(fā)展階段,,煥發(fā)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,,不僅成為中國傳統醫(yī)學寶庫中一顆耀眼的明珠,也成為世界醫(yī)學之林中一株挺立的雪蓮,。目前,,在西藏、青海,、四川,、甘肅、云南等主要藏族聚居地區(qū),,都設有藏醫(yī)醫(yī)院,,同時設有專門管理藏醫(yī)藥的衛(wèi)生行政機構。在發(fā)展藏醫(yī)藥的同時,,各級政府主管部門亦十分重視藏醫(yī)藥的挖掘整理與科學研究工作,,同時,大力發(fā)展藏醫(yī)藥教育,,在西藏,、青海、甘肅,、四川等省已建立了培養(yǎng)藏醫(yī)藥人才的醫(yī)學院或醫(yī)學系,,一些縣還設有藏醫(yī)學校,培養(yǎng)大學生、中專生等不同層次的藏醫(yī)藥專門人才,,使藏醫(yī)獨特的診療手段等得到了極大的發(fā)揮,。
.png)
(國家投巨資建立的西藏藏醫(yī)藥大學,經過30多年的發(fā)展,,已成為中國最大,、最權威的藏醫(yī)大學。圖片來源于網絡)
.png)
2006年5月20日,,藏醫(yī)藥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,。2007年6月5日,經國家文化部確定,,西藏自治區(qū)的強巴赤列為該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,,并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226名代表性傳承人名單。
.png)
(2018年11月28日,,中國“藏醫(yī)藥浴法”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,。圖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北京藏醫(yī)院藥浴科。圖片來源:央視新聞網)